 咨询热线: 18929573389 18928920971
咨询热线: 18929573389 1892892097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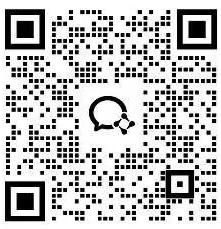
美国心理学家乔治·凯利的人格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人都是科学家”。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观察、假设、验证,试图创造一套理论来解释世间万物运转的规律,从而不断地接近真实。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在像科学家一样创立一套关于我们周围环境的理论,来帮助我们预期未来、减少不确定性。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关于周围世界的看法和解释系统,就好像是一份半透明的样板,试图用这份样板去适应构成世界的现实,这份样板凯利称之为“个人建构”。
作为科学家的我们,建构自己个人世界观的努力自我们诞生的时刻起就开始了。以孩童的天性,我们就像一块海绵,奋力吸收一点一滴的生活经验,通过观察、假设、验证,慢慢建立起对周围环境的认识。这种创造个人建构的过程与整个人生进程相伴。
机缘巧合之下,我接触到了心理咨询,开启了对自身的“个人建构”的重新审视的过程。
写下这篇文字之时,我已经完成了十二次心理咨询。是这十二次的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与我相伴的每一分钟,以及在此期间,心理咨询室之外的有意识的自我觉察和孜孜探索,让我能够对自己的人格有些微的洞察以及在行动上产生的改变。
这些洞察和改变,带给我未曾体验过的自由的感觉。

“如果我告诉别人我的需求,那就会有糟糕的后果。”
我的头脑中深深烙印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假设。
于是,童年时代,对于我越喜欢的玩伴,我越疏离。我是独生子女,父母离异,随母亲生活。我有两个表哥,分别长我七岁和八岁,是妈妈的两个姐姐的儿子。家庭之中并没有其他的同辈玩伴,我很喜欢和表哥们一起玩耍。
但是我从来不遵照家庭惯例称呼他们为“xx哥哥”,对于我来说这普通的称呼如此难以启齿。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妈妈为此苦口婆心教育我很多遍“你不能这样,人要有礼貌,你已经长大了,你不能这样做”。
我觉得妈妈说得对,但是我无法向人解释自己为什么觉得这样做很困难。时光流逝,哥哥们和我各自长大。而我,一直都还是那个不愿意称呼哥哥们的不礼貌的小孩,心里对这件事一直藏着愧疚和疑惑。
细细想来,让我难以启齿的不仅是对喜欢的哥哥们的称呼,还有所有和自己有关的需求,我都是能不说就不说。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超市,我从来不说自己喜欢哪样零食,对于每一种零食我都恨不得示以蔑视的态度,即使我知道自己很喜欢那一种裹了巧克力涂层的饼干棒。我也从不说我想要什么玩具,表达喜欢的方式走到对应的货架前停住,愣愣地看着它,然后妈妈会知道我想要那样玩具,我记得有一盒拼图就是这样买回家的。
在我过往行为模式中,这些普通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比如告诉别人我喜欢和你玩、我想要这个零食、我喜欢这个玩具等等,都是危险的事情,如果做了,就会产生糟糕的后果,可能是被拒绝,亦或是被斥责。
成年以后,我一度期望着遇到这样一个伴侣,我什么也不用说,他能够全然领会我的期待并满足我。省去了“表达我的需求”这个环节,让我感到更少的风险、更多的安全。
这样的习惯也让我很难融入一个新的集体。每次遇到需要融入新集体的时候,比如进入一所新的学校、加入一个新的社团、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单位等,我都会像蜗牛钻进壳里一般缩起来,但心里其实很希望能够结交新朋友。
如果这时候有人向我明确地发出表示欢迎的邀请,对我来说真的是旱地遇甘霖,我会既开心又感激。因为未被说出口的需求被他人的热情和善意妥善地接住了,我能够得到明确的被接纳的回应,而没有被拒绝的风险。但是这样的期待在大部分的时候都会落空。

“试试又能怎?”
“如果我告诉别人我的需求,那就会有糟糕的后果。”这是一条需要被更新的关于世界的假设。
科学家探索世界,建构着自己的理论;普通人在探索现实,建构着自己的生活。通过过去的经验我们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建构”,帮助我们预测未来。有些建构形成所依据的经验来自久远的过去,或许是童年时期,也可能更早。如果它们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生活环境,那么它们需要被更新。
“试试又能怎?”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心理咨询,有一天,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这样说。
于是,我像一只小心翼翼的蜗牛,慢慢从壳里探出头来,触角努力延伸多一点点,尝试主动向这个世界打声招呼。
在端午节瓢泼的大雨中我搬入了新家,远离了原来熟悉的社区环境和老邻居,我感觉到我需要一些新朋友。
出门倒垃圾时和出来拿外卖的隔壁邻居在电梯偶遇,我克服内心的犹豫,微笑着寒暄,对方有点社恐,眼睛不离手机,却也回答了我的招呼。
我邀请一些朋友来新家吃火锅,一开始总担心朋友们会在我家待得不开心,最后大家满意而归,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准备这次聚会的时候,发现家里凳子不够用,纠结了好几天是自己买一把还是向邻居借一把,最终,我敲开了新邻居的门,向他借一把凳子,对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社区群里有人在约晨跑,我斗胆说我也要加入,头天晚上心里很担心自己跑得慢跟不上别人,没想到最后只有两个人一起跑,对方还说我跑得很好。
我主动加入同事发起的羽毛球活动,头几次总是担心自己作为新成员会和别人配合得不顺利,人家作为长期的打球搭子早已互相熟悉,未必喜欢和我这个新人一起打球。直到参加了几次活动,慢慢发现我和大家水平相当,每个周末都一起打得很开心,我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与打球结识的新朋友一起走路回家的时候对方不怎么说话,我心里开始暗暗担心是不是她不喜欢我,然后就像开启了“情绪雷达”,不自觉地关注起对方的表情神态,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验证自己的担心。
后来发现这其实又是我的固有思维模式在作祟,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别人没有不喜欢我,只是刚好那时不怎么想讲话而已。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
一点点的改变,让我看到过去的观念并不是那么正确,新的行为模式带给我更为良好的体验。
如果我需要新朋友,我完全可以展示出友好的态度,主动寒暄、主动邀约、积极回应别人的请求,告诉别人,我欢迎你作为我的朋友。
不需要担心、不需要焦虑,没有什么糟糕的事情会发生。相反地,通过这样的尝试,我感受到了更多来自身边人的支持和接纳,来自内心的孤单感和对人际关系的疏离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我也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就像身上少了一副枷锁的轻盈。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这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心理咨询师建立的“安全、有信任、被接纳、受鼓励的咨访关系”以及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之上我对更完整、统一、自洽的人格的努力追求,让我看到卸下层层心理枷锁的希望。
这也印证了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所指出的重新审视个人建构的必要性,摈弃那些成形于旧有人生经验而不再适用于当下的部分,代之以更加符合当下情境和需求的对于世界的假设,可以让我们获得人格的成长。
下一篇: 你的电影口味,暴露了你的心理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