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咨询热线: 18929573389 18928920971
咨询热线: 18929573389 1892892097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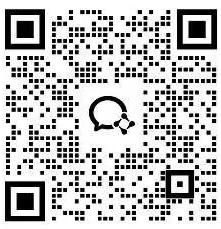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投射性艺术,其本质功能远超出简单的娱乐或叙事,它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剧场,观众在其中通过角色认同与情节共鸣,无意识地将内在心理内容外化到银幕形象上。
熟悉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朋友,或许会了解,电影观看中的认同机制提供了关键工具——银幕角色成为观众构建自我形象的"他者",通过这种想象性认同,观众得以在安全距离外探索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被压抑或禁止的情感与欲望。
陈可辛导演的《酱园弄》以其复杂的女性群像和深刻的时代叙事,成为当代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进行心理投射的绝佳载体。
以下,我将从精神分析视角出发,探讨不同女性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如何无意识地将内在期待、世界观和情感需求投射到詹周氏、西林和王许梅这三个核心角色上。

《酱园弄》作为一部以民国奇案为背景的女性群像电影,陈可辛导演的意图"恐怕不限于"简单的女性主义叙事,而是试图通过这个案件"展现一个特定中国时代的横断面,描绘洪流中众生的挣扎与浮沉"。
这种宏大的历史视角与微观的心理刻画相结合,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投射空间——影片中三位主要女性角色——被家暴后杀夫的詹周氏、知识精英西林和狱中"大姐大"王许梅——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的投射界面,不同背景的女性观众几乎都能在其中找到情感共鸣点。

当底层女性观众目睹詹周氏蜷缩在角落承受丈夫拳打脚踢的场景时,一种深刻的创伤共鸣在黑暗的影院中无声蔓延。
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这种强烈的情感反应远非简单的同情,而是潜意识的创伤重演——某些观众通过银幕形象重新体验自身被压抑的受害记忆。
这种投射过程虽然痛苦,却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将私密的创伤经验转化为可共享、可言说的文化叙事,是个体创伤社会化的关键一步。
正如一位观众所言:"看完电影后,我第一次敢跟别人说起前夫打我那些事了,因为突然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羞耻。"
这种从个人沉默到公共表达的转变,正是电影作为投射性艺术最深刻的社会功能。
詹周氏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人"(英文片名"She’s Got No Name"的隐喻)成为集体无意识中受压迫女性原型的当代具现,她的沉默与爆发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情感容器,容纳着观众难以言说的痛苦与愤怒。
当代社会中仍遭受家暴或经济压迫的女性,往往在詹周氏身上看到自己被压抑的反抗冲击力。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未简单美化这种暴力反抗,而是展现了其残酷后果——詹周氏最终不得不通过"诬陷他人"来求生,这一情节设置打破了"纯粹受害者"的神话,迫使观众面对反抗伦理的复杂性。
影片结尾处詹周氏与薛至武平视的镜头,成为这种受害认同的升华时刻。从精神分析视角看,这一视觉构图实现了"施虐-受虐"关系的象征性颠覆,满足了观众潜意识中对权力关系反转的渴望。
然而有趣的是,许多底层女性观众对这一场景的反应并非单纯的胜利感,而是复杂的悲悯——她们既认同詹周氏的短暂"胜利",又清醒意识到这种反抗的局限性。
一位受访者的评论颇具代表性:"她终于能直视他了,但代价是什么?整个系统还在那里。"
这种辩证认识显示了电影投射不仅激发情感释放,也可能促成对社会结构的批判性思考。

知识女性观众群体对西林这一角色的反应呈现出鲜明的爱恨交织特征。西林作为游走于汪伪政权名流圈的文化精英,其"假发浓妆"的社交形象与"关起门来利落短发"的私下面貌构成了一组精妙的人格面具隐喻。
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观众在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不得不穿梭于不同社会场域时的角色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真实性危机。
当观众批评西林"将詹周氏悲剧异化为个人晋升的跳板"时,实际上是在投射自身对职业成就与道德纯洁无法两全的焦虑。
西林以笔为剑为詹周氏发声的情节,触发了知识女性观众的救赎幻想与随之而来的幻灭。影片中她撰写《为杀夫者辩》并高呼"不要屈服"的场景,本应展现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却被不少观众解读为"表演性挑衅"和"口号式疾呼"。
这种批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精英负罪感——当现代知识女性通过西林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的社会活动可能同样流于表面时,产生的防御性贬低。

语言权力的议题在西林角色塑造中占据核心位置。影片刻意展现西林如何将自己的话语强加给詹周氏——在法庭上,这位文盲女性几乎是在"背诵西林写的文章"。
这一细节有观众尖锐指出:"西林为詹周氏设计的台词和她那些男权对手强加的叙事有什么区别?都是不让底层女性自己说话。"这种批评的激烈程度往往与观众自身的话语特权意识成正比。
西林角色的性别政治同样引发了知识女性观众的复杂投射。她宣称"我不缺男人"的宣言,既可以被解读为女性自主性的彰显,也可能被视为对传统性别游戏的妥协。
这种模糊性恰恰反映了当代职业女性在亲密关系领域的矛盾心态——如何在保持独立的同时不陷入新的异化?许多观众对西林情感生活的特别关注(“她到底爱不爱那些男人?”)暴露了自身对同类问题的未解困惑。
影片通过西林这个角色,将知识女性的情感觉醒与社会觉醒之间的不同步性戏剧化,为观众提供了审视自身情感模式的象征空间。

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观众对王许梅这一角色展现出特殊的亲近感,这种认同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触及生存策略的深层共鸣。
王许梅作为狱中"大姐大",其"不惜以身体换情报、以金钱买生机"的生存哲学,在精神分析视角下代表了一种原始适应机制——当超我的道德约束与残酷现实发生冲突时,自我发展出的实用主义妥协。
性工作者、前科者或处于灰色经济地带的女性往往在这个角色身上看到自己不得不做出的道德让步,并通过这种认同获得某种自我赦免。
影片中王许梅那句"想活,就要自己想办法"的台词,成为许多边缘女性观众反复引用的生存箴言,这句话剥离了道德外衣,直指生存本能的核心。

一位夜店工作者评论道:"你们中产女性可以谈女权理论,我们得先活下来。王许梅让我明白利用身体不一定是屈服,有时也是武器。"这种通过角色认同获得的自我辩护,显示了电影如何成为不同处境女性表达生存伦理差异的场域。
上一篇: 在人潮汹涌处,为何我们依然感觉孤独?